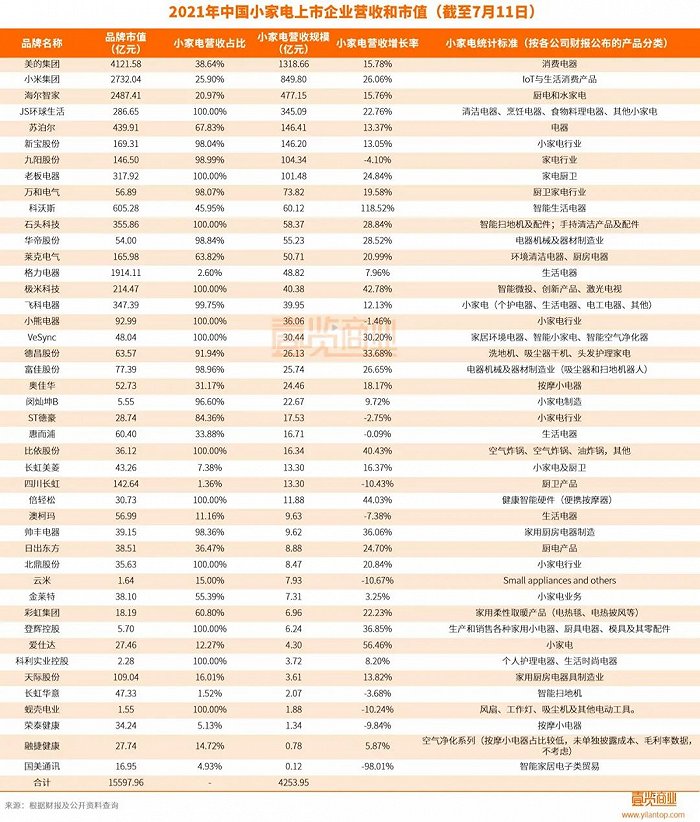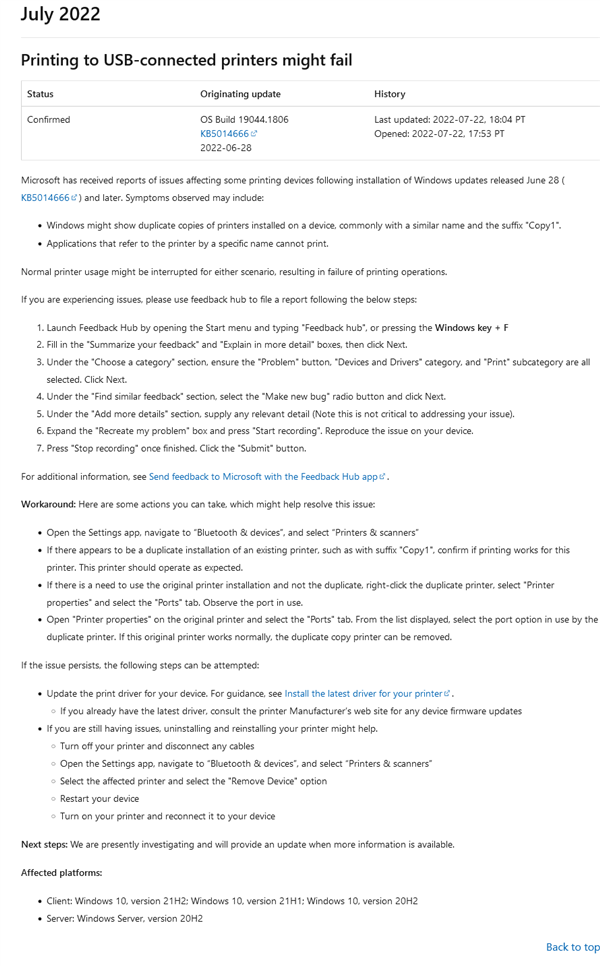1957年1月4日,在哥伦比亚物理系传统中式午餐聚会上,莱德曼从李政道那里听得吴健雄正在进行的宇称实验正取得了初步成果。他想要通过另一种方法来验证宇称是否守恒——观察自旋粒子π介子和μ子的衰变,正是李政道和杨振宁1956年论文中提出的其中一个实验设想。当天晚上,莱德曼构思了实验方案,如果成功,他们将看到“巨大的效应”。在*The God Particle: If the Universe Is the Answer, What Is the Question?*一书中,莱德曼详细回顾了这段经历,故事的结局是莱德曼和同事在四天内就见证了“上帝的破坏”,并且等待吴健雄检验结果后一起发表论文。本文仅介绍莱德曼在开车路途中是如何想到把实验的一连串奇迹变成现实的。
本文经授权摘自《上帝粒子:诺奖大师写给所有人的粒子物理趣史》(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6)中《间奏曲C:我们怎么在一个周末破坏了宇称并发现了上帝》一节,有删减,标题为编者所加。
撰文 | 利昂·莱德曼(Leon M. Lederman) 、迪克·太雷西(Dick Teresi)
 (资料图)
(资料图)
翻译 | 米绪军、古宏伟、赵建辉、陈宏伟
校者 | 尹传红
我无法相信上帝竟然是一个软弱的左撇子。
——泡利
所谓科学客观性的测试,就是不要让热情影响到方法论和自我批评精神。
——利昂·莱德曼
上海餐馆
又逢星期五。时间定格在1957年1月4日,中午12点。星期五是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的教工们传统的中式午餐日。10~15个物理学家先是聚集在李政道教授办公室的门外,然后结伴从第120大街的普平物理楼向山下的第125大街和百老汇大街路口的上海餐馆走去。午餐聚会始于1953年,当时李政道刚刚拿到博士学位不久,从芝加哥大学来到了哥伦比亚大学。这时的他作为理论巨星,已有了极高的声望。
星期五的午餐上人声嘈杂,人们三三两两地谈论着,享用着冬瓜汤的美味,品尝着游龙戏凤、小虾球、海参或是其他辛辣的中国北方大菜。在1957年,这些菜还不算太流行。在去的路上,我们已经很清楚这个星期五的交流主题了,那就是宇称和我们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当时正在华盛顿国家标准局指导一个实验的吴健雄所带来的最新消息。
在午餐会开始讨论严肃话题之前,李政道先在一个恭敬的餐馆领班递来的小便笺本上点菜——每星期来吃饭他都要干这些琐事。李政道点菜很有派头,那真是一种艺术。只见他瞅了一下菜单、便笺本,用汉语向服务员问了一个问题,而后皱皱眉头,提笔画过纸面,认真地写了几个符号。接着是另一个问题,在一个符号上做了一下改动。为了得到神的指引,他瞥了一眼锡制的浮雕天花板,然后,大笔一挥而就。最后再看时,他的两只手都停在便笺本上,一只手五指伸开,传递着教宗对众人的祝福,另一只手则握着铅笔杆。一切尽在此间?阴阳和色香味的完美交融?把便笺本和笔都递给服务员以后,李政道加入谈话中来。
“吴女士打电话告诉我,她的初步数据表明了一个惊人的效应!”他兴奋地说。
让我们回到那个一面墙上有块镜子的实验室(上帝创造的那个真实的世界)吧。我们的一般经验是,不论我们对着镜子举起什么,不论我们在实验室里做何种实验——散射、制造粒子、像伽利略所做的那类重力实验,等等——镜中实验室里的一切都遵从同样的支配真实世界的各种自然定律。我们先来看一下违背宇称守恒是如何表现出来的。为了给手性做一个最简单的客观测试,不妨找一个“特维洛”星球的居民,让他使用一个右旋的螺钉。现在,他面对着打洞的一端,顺时针旋转螺钉。如果螺钉钻进一块木头里,则将其定义为右旋螺钉。显然,镜子里展现的是一个左旋螺钉,因为镜子里的那位“特维洛”居民正在逆时针旋转螺钉,且螺钉也钻进去了。好,现在假设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可思议的世界(比如《星际迷航》中的幻想星球)上。在这里不可能使用一个左旋的螺钉——完全与物理定律背道而驰。这样,镜像对称将被破坏;右旋螺钉的镜像将不会存在,而宇称守恒则被破坏。
这就是前奏。李政道和他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同事杨振宁建议检验一下弱相互作用下物理规律的有效性。我们需要右旋(或左旋)粒子的等价物。像机械螺钉那样,我们需要把旋转和运动方向组合起来。考虑一个自旋的粒子——μ子,把它看作一根绕着自己的中心轴自旋的圆柱体,我们就有了旋转。因为μ子圆柱的两端是完全相同的,我们不能说它是顺时针自旋还是逆时针自旋。为了弄明白这一点,你可以把它放到你和你最喜欢的一个对手之间。当你发誓说它是向右旋转(顺时针方向)的时候,他却坚持它是朝左旋转。没有什么办法争出个你对我错来。这是一个宇称守恒的情况。
李、杨的天才就是:通过观察自旋粒子的衰变,引入(他们想要检验的)弱相互作用。μ子的一个衰变产物是电子。假定大自然命令电子都只从圆柱的一端跑出来,这就给定了一个方向;而且,我们也就可以确定自旋的概念了——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因为一端已经被定义(电子出来的方向)。这一端起到了螺钉钉尖的作用。如果相对于其刚刚衰变出来的电子,μ子的自旋方向向右(顺时针),就像机械螺钉相对于钉尖的旋转,那么我们就已经定义了右旋的μ子。现在,如果这些粒子总是按照定义的右手性方式衰变,那么我们也就有了一个违背镜像对称的粒子过程。这是我们在μ子的自旋轴平行于镜面时看到的情形,镜子中的像是一个左旋的μ子——但它并不存在(如下图)。
镜中实验与宇称守恒
虽然有关吴健雄的情况在圣诞假期前后就已经传开了,但新年后的星期五是放假后物理系的第一次聚会。1957年,吴健雄像我一样在哥伦比亚大学任物理学教授,她是一名很有建树的实验科学家。她的研究专长是原子核的放射性衰变。她精力异常充沛,对学生和博士后要求很严格。在分析实验结果时,她也相当仔细、认真,她发表的实验数据以准确性高而广受赞誉。
1956年夏天,当李政道、杨振宁挑战宇称守恒的正确性时,吴健雄几乎马上就着手验证。她选择不稳定的放射性原子钴60的原子核作为实验对象。钴60的原子核会自发地衰变为一个镍核、一个中微子,以及一个带正电的电子(正电子)。我们能“看到”的是,钴核会突然放射出一个正电子。这种形式的辐射被称为β衰变,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放射出来的电子不论正负最初都被称为β粒子。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物理学家称其为弱相互作用,并认为有一种可以引起这种反应的力作用在自然界中。力不仅仅是推和拉、吸引和排斥,还可以引起物质种类的改变,如钴变成镍并辐射轻子的过程就是这样。从20世纪30年代起,大量的反应被归因于弱相互作用。伟大的美籍意大利科学家费米率先给出了弱相互作用的数学形式,这使得他可以预言像钴60发生的这种反应的许多细节。
李政道和杨振宁在他们于1956年发表的论文《弱力中的宇称守恒质疑》里,挑选了一系列反应,并检查了实验中宇称——镜像对称——不受弱相互作用支持的蛛丝马迹。他们感兴趣的是从自旋的原子核里放射出的电子的方向。如果电子更偏爱其中一个方向,那就像是给钴核穿上了缝有纽扣的衬衫。这样的话,我们也就能够说出哪个是真实的实验,哪个是镜像了。
是什么区别了普通的科学工作和伟大的思想?对一首诗、一幅画、一支曲子也可以问类似的问题——实际上,甚至连法律诉状之间也会有天壤之别。艺术作品要靠时间去最终裁定;而在科学中,一个思想、一种观念的对错则要由实验来判定。如果它是光辉的思想,那么往往就会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催生一大批新的问题,而一大堆老问题则迎刃而解。
李政道思维缜密,无论是午餐时的点菜,评论一些中国古瓷器,抑或是评价一个学生的能力,他的观点都锋棱崭然,有如巨匠运斤,不差分毫。在李政道和杨振宁(我不是很了解杨振宁)关于宇称的论文里,那宝贵的思想就有许多尖锐的观点。他们靠中国人的那股子冲劲,质疑一个曾经认为是牢不可破的自然定律。李政道和杨振宁意识到,所有这些已导致“构造完善”的宇称定律的大量数据,与引起放射性衰变的自然现象即弱相互作用毫无关系。这又是一个闪光而尖锐的观点:它第一次让我们明白,自然界不同的力可以有不同的守恒定律。
李政道、杨振宁挽起袖子上阵,汗水涔涔,灵感不断。他们查验了大量有希望用来测试镜像对称的放射性衰变反应。在论文里他们还十分细致地分析了可能的反应,以便保持沉默的实验家能够检验镜像对称是否有效。吴健雄设计了其中的一个实验,她使用的是钴的反应。她的方法的关键是确保钴核——哪怕只有很少的一部分钴核——能以同样的方式自旋。吴健雄提出:要确保这一点,可以让钴60源在极低温度下工作。她的实验极其精密,需要用到很难找到的低温装置。为此她求助于国家标准局——那里拥有非常先进的自旋调节技术。
那个星期五宴席上的倒数第二道菜,是用黑豆酱油加上葱和韭菜焖出的大鲤鱼。在上这道菜的时候,李政道反复强调了这一关键信息:吴健雄发现的效应非常显著,超出我们期望的10倍以上。虽说数据还没有看到,是试探性的,而且还很初步,但(李政道给我夹了鱼头,他知道我喜欢)如果效应的确非常显著的话,就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如果中微子是两种成分……我听着听着就走神了,不知道他继续在说些什么,因为一个新的想法渐渐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巨大的效应
午餐之后还有一个专题研讨会、系里的一些例会、一个社交茶话会,以及一个学术讨论会。所有这些活动我都心不在焉,心里一直挂念着吴健雄正在观察一个“巨大的效应”。8月份李政道在布鲁克黑文的谈话,让我想起了宇称会在π介子和μ子衰变时缺失的那个想法。我们一度忽略了它。
巨大的效应?8月份我曾经粗略地看过π-μ衰变链,并且意识到应该设计一个合理的实验,要在两个连续的反应中有宇称破坏。我一直在回忆8月份我们曾经做过的计算。然而,倘若效应非常显著的话……
下午6点左右,我驱车向北行驶,回到位于多布斯费里的家中吃晚饭。然后,又在这个寂静的夜晚前往哈得孙河畔欧文顿的尼维斯实验室跟我的研究生换班。尼维斯实验室中的400兆电子伏加速器是生成介子及研究其性质的主力干将,20世纪50年代,介子可是一种相当新的粒子。在那些快乐的日子里,只有几种介子值得关心,而尼维斯关注的是π介子和μ子。
在尼维斯实验室,我们拥有高强度的π介子流,它们出自一个被质子轰击的靶。π介子并不稳定,它们从靶里飞出,脱离开加速器,穿过屏蔽墙,再进入实验厅,其间有大约20%的粒子经历了弱衰变,转变为一个μ子和一个中微子。
π→μ+ν(在飞行过程中)
μ子通常与π介子沿同一方向飞行。如果宇称规律被推翻,自旋轴的方向与运动方向一致的μ子数量,就会多于自旋轴的指向与其飞行方向相反的μ子的数量。如果效应巨大,大自然或许会给我们提供粒子全都以同样方式自旋的一个实例。这就是吴健雄把钴60冷冻在温度极低的磁场里的情形。关键是要观察到已知自旋轴方向的μ子衰变为一个电子和一些中微子。
灵感诞生于途中
星期五晚上,从索米尔河公园路驱车向北,一路上车水马龙,甚是繁忙,沿途能够模模糊糊看到为森林所覆盖的美丽丘陵。这条路沿着哈得孙河蜿蜒曲折,经过里弗代尔、扬克斯径直向北。途中我盘算着可能的“巨大效应”,不时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对于自旋的物质来说,如果有任何一个方向的自旋轴在粒子衰变中占优势,那就会呈现出这种效应。一个不明显的效应可能是,相对于自旋轴的方向,在一个方向上射出的电子有1030个,而另一个方向有970个,这就很难下结论。但一个巨大的效应就是说1500∶500,这样情况会简单得多。这个幸运的巨大效应还将有助于安排μ子的自旋。要做这个实验,我们需要所有μ子都朝一个方向自旋的实例。由于粒子要从回旋加速器运动到我们的装置里,因此μ子的运动方向可以作为μ子自旋的参照。我们需要大多数μ子都是右旋的(或者都是左旋的,这无关紧要),现在把运动方向看作“大拇指”。μ子将会飞出去,通过几个计数器,最后在一个碳块里停下来。而后我们数出有多少电子沿着μ子的运动方向出现,又有多少电子以相反的方向出现。数量的巨大差异将是宇称破坏的证据。然后,我们就会声名远扬,好运不断!
突然,一个念头搅乱了这个普普通通、安宁静谧的星期五夜晚,我想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做这个实验。我的研究生马赛尔·温里克(Marcel Weinrich)一直在做一个跟μ子有关的实验。他的实验装置稍加改造就可以用来寻找那个巨大的效应。这时我又回顾了用哥伦比亚大学的加速器制备μ子的方法。作为这方面的专家,很多年以前我就跟丁洛特一道设计过外来的μ子和π介子束,那时的我还是个鲁莽的研究生,而机器也是崭新的。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了整个过程:一座加速器,带有一块重达4 000吨的磁体,圆形磁极的直径约有20英尺,加速器里面夹着一只巨大的抽空了空气的不锈钢箱子,即真空腔。一个由微小管道注入的质子流进入磁体的中心。质子在很强的射频电压下反复冲刺,螺旋式前进。当粒子到达螺旋式旅途的终点时,已经具有400兆电子伏的能量。在真空腔的边界附近,我们的磁体基本上鞭长莫及的地方,一根载有石墨片的小棒等着被高能质子轰击。它们所具有的4亿伏高压,足以使这些高能质子在与石墨靶上的碳原子核相撞时产生新的粒子——π介子。
此刻我仿佛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π介子在质子的冲击下向前喷射的一幕。它们在回旋加速器强大磁体的磁极间诞生,沿着一条舒缓的曲线飞掠而出,消失在回旋加速器之外。那里随即出现了μ子,继续着π介子的未尽之旅。磁极片外迅速消失的磁场使μ子沿着隧道穿过10英尺厚的混凝土防护墙,来到实验大厅,在这里我们已经恭候多时了。
实验室里,马赛尔正在启动设备。μ子会慢慢地落到一个3英寸厚的滤波器里,然后被送到一块含有各种元素的1英寸厚的材料里暂存。μ子会与材料里的原子温和地碰撞而失去能量,并由于带有负电荷而最终被带正电荷的原子核俘获。由于我们不想让任何东西影响μ子的自旋方向,而被俘获进轨道则是毁灭性的,所以我们要使用带正电荷的μ子。带正电荷的μ子会做什么呢?可能就是在那里默默自旋直到衰变。材料必须谨慎选取,碳看起来就很合适。
现在,一个关键的想法浮现于我这个在1月的某个星期五驱车北行的司机的脑海里。如果在π介子衰变时产生的所有(或几乎所有)μ子能够以某种方式把自旋调整成同一方向,那就意味着π介子到μ子的反应违背了宇称守恒,并且是严重地违背。一个巨大的效应!现在,假设μ子沿着优美的弧线飞出机器穿过隧道的时候,它们的自旋轴与运动方向保持平行(如果g因子接近2,这就是会发生的实际情况);再进一步假设,μ子与碳原子发生的数不清的温和碰撞,在使自己逐渐慢下来的同时,并不影响自旋与运动方向之间的关系。如果这一切真的发生了,那就太离奇了!我就会有了一个让μ子进入材料块里暂存,并以相同方向旋转的方案。
看起来,一个成功的实验似乎需要一连串的奇迹。的确,当8月份李政道和杨振宁宣读他们那蕴含着小效应的论文时,因为需要这种一连串的奇迹而让我们感到灰心丧气。一个小效应还可以被耐心征服,而两个连续的小效应——如百分之一的百分之一——则会让实验希望渺茫。为什么是两个连续的小效应呢?回想一下,大自然得提供这样的π介子,它们能衰变成自旋方向大体一致的μ子(奇迹一);μ子还必须能衰变成这样的电子,它们相对于μ子的自旋轴明显不对称(奇迹二)。
经过扬克斯收费站(1957年时收费5美分)的时候我变得激动万分。我真的感到非常肯定,如果宇称破坏是明显的,那么μ子就是极化的(自旋轴指向同一方向)。我还弄明白了μ子自旋的磁特性,乃是由于磁场作用把其自旋方向都“扳”到粒子运动方向上去的缘故。至于μ子进入吸收能量的石墨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还没有太大的把握。如果我弄错了,那μ子的自旋轴就会五花八门。真要是那样的话,就无法观察电子相对于自旋轴的放射了。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π介子的衰变产生了自旋方向与运动方向一致的μ子,这是奇迹的一部分。现在我应该让μ子停下来,以便观察它们衰变时放射出来的电子的方向。由于我们知道它们在撞击碳块之前的运动方向,所以,假如没有什么东西使它们发生转动的话,我们就会搞清楚它们停下来发生衰变时的自旋方向。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在碳块周围转动我们的电子检测臂,那里μ子正等着检查镜像对称呢。
我重新思考着要做的事情,手掌心开始出汗。计数器全都有了。那些告诉我们高能μ子到达后缓慢进入石墨块的电子器件,现在已经就位并顺利通过测试,用于检测μ子衰变产生的电子的由4个计数器构成的“望远镜”也有了。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些东西按一定的方式固定在一块板子上,再把它围绕石墨块的中心安装好。只需一两个小时的工作。喔!可我觉得,我们又将度过一个不眠之夜!
特 别 提 示
1. 进入『返朴』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精品专栏“,可查阅不同主题系列科普文章。
2. 『返朴』提供按月检索文章功能。关注公众号,回复四位数组成的年份+月份,如“1903”,可获取2019年3月的文章索引,以此类推。
版权说明:欢迎个人转发,任何形式的媒体或机构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和摘编。转载授权请在「返朴」微信公众号内联系后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