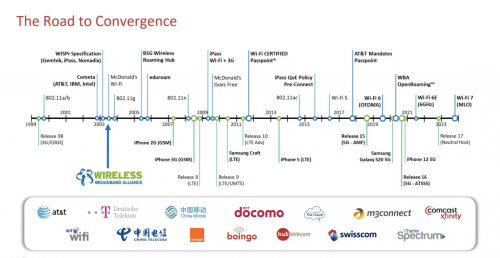**人物简介:**牛煜琛,高校科幻平台编委,和光读书会成员,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传播学2021级硕士研究生,师从王瑶副教授(笔名“夏笳”)。作品曾获第十届光年奖校园之星优秀奖、第十届未来科幻大师奖三等奖等奖项,有评论文章见于《文艺报》《香港文学》等刊。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高校科幻: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科幻的?
**牛煜琛:**如果“科幻”指的是那些门类清晰的科幻文本,那凡尔纳的作品应该是我和大多数人共同的起点。初中的时候比较喜欢看网文,那时对一些作品里的科幻元素还没有特别在意。后来到了高中,大刘得了奖,我才开始有意地阅读一些科幻作品。第一部自己主动找来读的科幻作品应该是大刘的短篇集《2018》,那之后就会经常地找一些国内外的科幻作品来看了。但另一方面,科幻的想象力对我的影响,也许在我正式接触科幻作品之前就已经发生了。比如小时候看过的童话《皮皮鲁和幻影号》、《皮皮鲁与机器猴》,虽然是儿童文学,虽然缺少很多科幻作品所提倡的科学性,但其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以及对人与人工生命、人与自然环境等科幻命题的思考和讨论等,都是很有价值的。
高校科幻:您读过哪些印象深刻的科幻作品?
**牛煜琛:**关于印象深刻的科幻作品确实有很多:阿西莫夫的《最后的答案》和《终极问题》,布雷德伯里的《霜与火》,何夕的《伤心者》……还有在《时间不存在》上看过的滕野的一篇短篇(《时间之梯》),那篇结尾给我留下的印象还是挺深刻的。卡尔维诺《宇宙奇趣全集》里有很多篇都很难忘,比如《太空里的一个记号》、《恐龙》、《世界的记忆》(虽然它们应该不算一般意义上的科幻)。科幻电影里印象最深的一定是《2001太空漫游》,此外,个人觉得这部电影的美妙更胜于克拉克的小说。我认为比起简单地去阅读故事或接受知识,这种“科幻的想象力”无疑更能激发我们对科幻、科学以及人类文明本身的求知欲。
高校科幻: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科幻的?之前有其他类型文学的创作经历吗?
**牛煜琛:**大三时确定了将来的研究方向应该算是一个关键节点。接触“科幻研究”大概是在2020年的寒假。当时为了准备毕业论文,把各种科幻经典、科幻文学史和相关的论文专著恶补了一顿,同时也在那个寒假尝试创作了自己的第一篇大约三万字的科幻短篇。在有意地进行科幻创作之前,我其实已经积累了一些写小说的经验,不过之前尝试的都是历史演义、武侠、古风言情这种类型,那时候比较中二,网文痕迹也很重——虽然现在好像也没改善太多。
高校科幻:您第一次创作科幻作品的初衷是什么?
**牛煜琛:**第一次写科幻的目的其实有点不好评价。一方面我只是单纯想试试新的写作模式,但另一方面也确实存了想在这个圈子写出点名堂的心思。当时刚好赶上《赛博朋克2077》正式发售,“赛博朋克”的概念成为了一时热潮,加上我在写毕业论文的过程中也对这种风格的作品和文化有过一定了解,那自然而然,我就想写一个发生在同类世界观之下的故事。另外当时我觉得,既然是“第一次”,写爱情故事肯定不会犯错,于是就写了《至爱西比尔》这样一个永生者与赛博格生死相逐的故事。简单来说,那个故事其实就是科幻背景下的《麦琪的礼物》,但现在看来,我把背景过于复杂化了,反而使叙事变得冗烦、矛盾变得模糊,因此大概算不上成功的“第一次”。
高校科幻:文学之外的其他艺术形式,如音乐、绘画、戏剧、影视等,对您的创作有何影响?
**牛煜琛:**相较于传统、古典的艺术,现代流行艺术和文化对我的影响可能会更大一些。因为我觉得时下正在生成的、还没有被固定在文学和艺术史中的文化现象,本身就具备一种成为先锋的潜力和可能性。而且从整体来看,今天的文化与过去种种之间,更多地呈现为对抗、颠覆以及解构的关系,在观察、或者说欣赏这些矛盾与冲突时,往往更容易获得创作的激情。具体些来说,比起传统的绘画、雕塑以及戏剧,我觉得电影艺术对今天写作者的影响会更加明显。
高校科幻:您格外看重电影艺术,在您眼中它有何独特的价值?
**牛煜琛:**比如如何用文字塑造故事的氛围感、还原画面的质感,如何兼顾戏剧冲突与细节伏笔的编排……就我个人而言,无论是设计一个情节、一个人物,还是想象一个场景,首先在脑海中形成的往往是一个上帝视角的虚拟剧场,我永远在“第四面墙”外充当观众、导演,而非参与其中的演员。换句话说,我认为镜头语言已经成为了现代人想象世界的第一道窗口。曾经人们热衷于讨论诗与画、动与静、时间与空间的界限,而现在这个问题又发展(也许是回归)了许多,于是人们的想象力、对内容与形式的理解、对创作的要求和评价标准都随之发生了变化,仿佛一切终于汇流,“互文”的对象从小说文本,拓展到诗歌、戏剧、电影、音乐、技术,甚至社会新闻、漫画、游戏之中,没有什么不能成为写作的对象和灵感的来源,而科幻的想象力则尤其适用于驾驭这一切。
高校科幻:可否结合您的具体作品谈谈各种文艺作品是如何影响您的创作的?
**牛煜琛:**如果拿我自己并不丰富的创作举例,《至爱西比尔》的故事本身模仿的是《麦琪的礼物》,而人文内核源于艾略特在《荒原》开头的用典(相传女预言家“西比尔”从阿波罗那里得到了长久的寿命,但忘记了同时要求不朽的青春,遂不得不堕入衰朽的永生中),至于其世界观及技术则是借鉴了《赛博朋克2077》那款游戏。当下无论是艺术的“内容”或者“形式”都正在趋于消解,但这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好处,即实用主义的创作原则,这是一个真正应该“浅深聚散,万取一收”的时代,而在碎片构成的洪流之上,我相信科幻将是最自由的一种写作方式。
高校科幻:您就读于文学专业,是什么让您选择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牛煜琛:**顺其自然吧。高中文理分科选了文科,然后本科的时候,我们大一的专业是新闻传播类,大二会分流成汉语言文学(就是俗称的“中文系”)和广播电视学两个专业。当时也没有太多考虑,觉得中文系的老师和课程都更有意思一点,加上我本身在文学方面有一定积累,所以就学了中文。因为是自己的选择,所以我对于这个专业从来没有过抵触,学习起来也比较轻松愉快,加上文学本身就是极富魅力的一种学问,所以很快也就热爱上了。至于从读者到创作者的身份转变,其实也和我的专业有直接联系。大一时我们就有一门中文系的课,叫做“创意写作”,当时给我们授课的两位老师为了激发同学们的创作欲,对每份作品都很认真地点评、反馈,也组织过小规模的作品互评会。是修习这门课的经历启发了我,原来接触文学的途径不止是阅读、批评、研究,还可以是创作。再后来,我就开始尝试创作新诗、剧本、散文、网络小说,当然还有科幻小说。尤其是开始尝试科幻后,运气比较好,在学校外面拿了几个奖项,算是获得了一些新的正面反馈,所以现在也还没有放弃写作。
高校科幻:您是习惯日拱一卒的计划型创作,还是灵感驱动的激情型创作?
**牛煜琛:**应该说,更习惯前者,但更享受后者吧。相比起任务驱动型的写作,我感觉自己写文的动力更多还是内发性的,但可能因为天分不够,所以很少有那种能文不加点、倚马既成的情况。大多数时候,我都是想到一个点子或者一个片段化的场景,就先把这部分记下来,然后再完善大纲、制定创作计划,给自己设定每天大约的任务量,以防最开始的想法流产。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觉得想象是愉悦的,但码字确实是痛苦的,要将那些想法落确成文字,用语言一点点构筑一个场景、对话、故事,需要耗费的功夫并不比写论文更容易。尤其是当最初的创作冲动冷却下来后,要继续完成这个故事或许靠的就是毅力了。这种时候通常会产生一种在和谁进行某种交易的错觉:作为代价,写作的热情和快感逐渐消耗,经由空乏的文字,勉强置换出一篇不甚成熟的故事,然后原本灵感驱动的激情型创作也就不得不过渡到了日拱一卒的艰难阶段。但我认为自己迄今为止的写作实践多少还是有值得庆幸的地方,比如,不论最终写出来的故事是否令自己满意,至少我没有放弃过任何一个灵感,也还没有在任何一个故事尚未完结时就半途而废。
高校科幻:哪些因素造就了您现在的创作习惯??
**牛煜琛:**关于创作习惯的问题,我觉得影响最大的因素大概是表达欲吧?另外,我喜欢在凌晨一个人的时候写作大概也和这点有关。白天接受信息和与人交流的渠道太多了,甚至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通过同他人交流来维系所谓的日常生活。这就好比酿造果酒的过程,白天的确能够产生很多想法、很多念头,也许这些念头同样可口、诱人,但它们过于新鲜,而仅仅从树上把果子摘下来,是无法得到我们所追求的那种东西的。因此,我们需要时间、等待,还有沉默,在无人声处、无字句处,把白天的各种念头一并压碎,榨取出有潜质成为佳酿的部分,然后使其发酵,从破碎重新变得完整,最后,酝酿成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存在。在这其中,我认为最关键的就是“沉默”,也就是控制和积累表达欲。当一个人在现实中表达过剩的时候,他其实是不适合写作的,因为他可能已经在别处把想说的话都说尽了,或者更遗憾的是,他将过剩的表达欲带入了写作当中,导致所有文字都变成了一个人自娱自乐的刻奇表演。“冰山理论”、“零度写作”、《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里面的“轻逸”与“迅速”……太多写作者已经用他们的作品和理论证明了克制的必要性,当然,我自己也在学习和尝试,尝试保持沉默,让思想的归于思想,语言的归于语言,然后在我需要的时候,真正化为充实的、能够用于表达的力量。
高校科幻:您是如何看待“科幻文学”在文学领域的地位,以及它与其他文学领域的联系的?
**牛煜琛:**即使今天,我们也必须承认,无论是作为类型文学,还是作为一种流行文化,科幻都没有摆脱“边缘”的身份,但我认为,科幻的“边缘”地位自有其必然性与必要性。从诞生之初,科幻小说就是以主流文学为客体对象而得以观照出的自身。当我们谈论科幻时,其实就是在直面现代文明的可怖罅隙,直面人性与真理的真空地带。就像吴岩老师在《科幻文学论纲》的序言中所说,“科幻在许多方面跟主流文学保持恰当的距离,这反而给它在大文学中确定了独特的、无可替代的位置”。无论出于被动或主动,这种“恰当的距离”都使科幻不得不成为一种边缘和底层,但我们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个开放的边缘,一个足够富于多元化可能的底层,也因此才拥有无限发展的空间。
高校科幻:您是如何看待“科幻”与“科学”之间的关系的?
**牛煜琛:**科幻文学总是拒绝表现迎合当下潮流的赞歌式理想,它总是在科技的希望将萌未生时大胆畅想明天,但在民族与文明高歌猛进时却又充满对未来危机的忧虑,其沦为“边缘”的必然可见一斑。除此之外,如果回归其文类本身特质,科幻文学之为“边缘”同样有其内在原因。身为自然科学与文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交集产物,科幻小说作为思想的载体并不总是能平衡好科学与其他思想的权重关系。相反,虽然现代科学从一开始就在科幻小说中获得了权力主体的位置,但正如所谓“科幻原教旨主义”与其反对者之间的分歧,科技与人文在现代社会中的对应位置,注定了科学与文学、技术与伦理将存在长久的矛盾,同时也决定了科幻只能成为被两者皆所不容的异类,换句话说,只有徘徊在交集区间,亦即“边缘”时,科幻才能成为它自己。
高校科幻:您未来会坚持科幻创作吗?有无一段时期内的创作计划?
**牛煜琛:**应该会坚持吧,或者说我希望自己未来能够不要放弃创作。最近大概有两个故事想完成,一篇中篇和一篇短篇。中篇的设定有关语言,大概讲述人类因为失去语言而变得团结,最终在宇宙间寻回失去的语言的故事。短篇的灵感来自“举头见日不见长安”的典故,想以未来的西安城为背景,将西安与长安这组空间对照移位至未来,从旅行者的视角设计一个科幻寓言。
高校科幻:您对当前特殊的疫情时代和未来的后疫情时代有何感触和展望?
**牛煜琛:**疫情时代属实不好评价,虽然莎翁有“身虽囿核桃,身为无限王”的名句,但离开文学,很难说空间上的局囿不会对我们思想的宽度有所影响。去年冬天我在西安上学,刚好经历了一个月的封城,在有限的外出时间里,我站在天桥上,静伫而对的大厦与旷远的街道构成了现代都市极为少见的奇观,时间仿佛凝滞,过去种种在此洄游,孕育着似曾相识的明天……立身“空城”,如在旷野,有限且短暂的自由里,钝化的官能终于得到新的启发,我才意识到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早已失去了创造与探索新知的激情,此前的思想仅仅是在一种惯性下勉强维持着动态的表象而已。对于未来,我不敢奢望所有人都能弥补上自己人生可能性中已然缺失的部分,只希望我们还能有足够的自信和心气重新上路,无论明天会更好,还是更烂。
高校科幻:您担任了星火杯比赛复审评委,您与高校科幻和星火杯是如何结缘的?您对高校科幻和星火杯有什么建议和期待?
**牛煜琛:**今年是我第二次星火杯之旅。去年,也差不多是我刚开始写科幻的时候,一个学长给我安利了这个比赛。当时很遗憾,初审折戟了,但也因为这个比赛接触到了高校科幻平台以及认识了一些可爱的同好们。我觉得这个比赛最大的意义就在于此,对很多高校的科幻迷来说,这是一个因热爱而建立的聚集地,也是一个踏入科幻写作的良好起点,文字或许存在参差,但思想和热爱则不分高卑。我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人因高校科幻和星火杯而与彼此、与科幻结缘,而那些来自同行者的目光也将成为新的星星之火,终以燎原。
采访:赵晓宇
编辑:赵晓宇